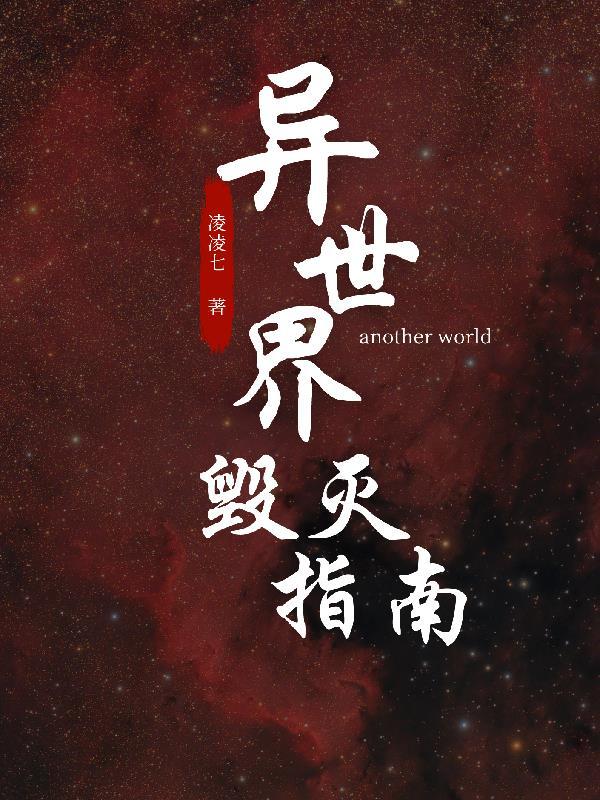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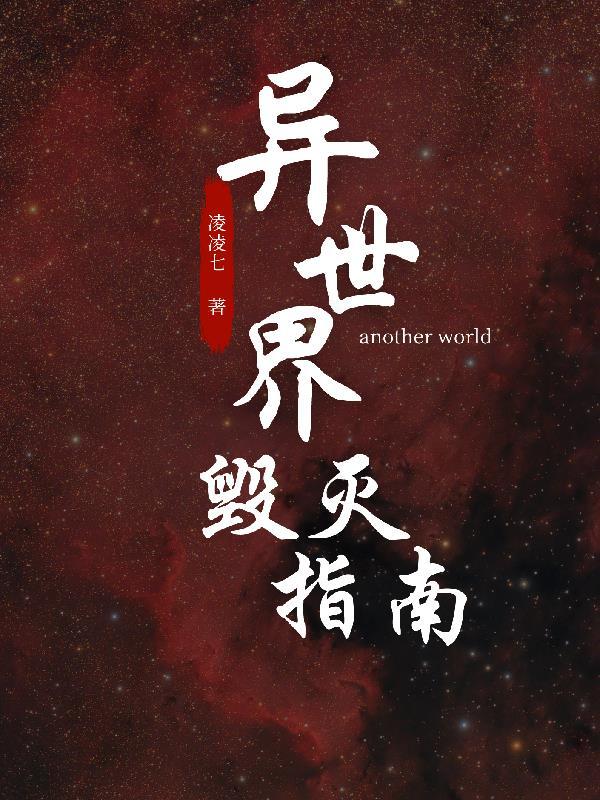
我隔着毯子伸出手,按铃叫来吉夫斯。
“晚上好,吉夫斯。”
“是早上好,少爷。”
我吃了一惊。
“天已经亮了?”
“是的,少爷。”
“没搞错吧?看着外面还黑乎乎的。”
“少爷,外面起雾了。少爷记得的话,现在已经入秋了,正是‘雾气洋溢、果实圆熟’的季节[1]。”
“什么季节?”
“雾气洋溢,少爷,果实圆熟。”
“哦?啊,对对,懂了。嗯,就算是吧,你那个提神剂给我来一杯,好不好?”
“已经备好了,少爷,在冰箱里冰着。”
他倏忽一闪就不见了。我坐起身,有种偶尔浮现的那种不舒服感,就像自己不出五分钟就要毙命似的。昨天晚上,我在螽斯俱乐部里请果丝·粉克-诺透吃饭,为他饯行,他马上要同沃特金·巴塞特爵士(大英帝国二等勋爵)的独生女儿玛德琳喜结连理。这种事儿呢,总是要产生一定后果的。不错,吉夫斯进屋之前,我正梦见有个恶棍往我脑袋里钉橛子,而且钉的还不是像基尼人希百之妻雅亿[2]用的那种普通橛子,而是烧得通红的橛子。
吉夫斯端着还魂剂走进来,我咕咚咚灌进喉咙,初有略略不适之感——喝下吉夫斯的专利续命饮之后这种感觉总是少不了的:头盖骨朝天棚飞升,眼珠子从眼窝里弹出去,又像回力球似的从对面墙上弹回来;这下舒服多了。不过,要说伯特伦现在恢复到了最佳比赛状态,那还是有点牵强,不过至少是恢复了点儿元气,有精神说会儿话了。
“哈!”我接住眼珠子装回原位,“哎,吉夫斯,这大千世界有什么新消息?你拿的是报纸吧?”
“不,少爷。这是旅行社的一些读物,我想少爷可能乐意扫一眼。”
“哦,”我说,“你这么觉着是吧?”
接下来是片刻的沉默,好像孕育着什么——这个词好像没用错吧。
这么说吧。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两位男士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,偶尔爆发些小摩擦在所难免,而最近伍斯特府上就爆发了一桩。吉夫斯想叫我去参加什么环游世界的邮轮之旅,我断不同意。可是虽然我坚决予以否定,但是他没有一天不给我弄那么一两束或者一两把折页插图宣传册,都是那些个宣传“啊,广阔大自然”的家伙散发来招揽顾客的。总之,吉夫斯的做法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锲而不舍的猎狗,坚持叼一只死耗子摆在客厅地毯上,丝毫不管主人家如何用言语、手势孜孜教诲,说明死耗子这会儿不时兴,其实嘛从来都不时兴。
“吉夫斯,”我说道,“以后不许拿这事儿烦我了。”
“旅行极有教育意义,少爷。”
“我不能再受教育了,多年前就受够啦。吉夫斯,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。你那点儿维京海盗的血统又出来作祟了,渴望去呼吸点儿咸咸的海风,幻想着自个儿在船头甲板上散步。也可能谁跟你念叨过巴厘岛的舞女来着。我都懂,我很理解。但是不行。我拒绝把自己关进该死的远洋船里,被拖着满世界跑。”
“遵命,少爷。”
他的语气里有一点儿那什么,我感到他就算不是心中不快,也远远说不上心中大快,因此便机智地转开了话题。
“哎,吉夫斯,话说昨天晚上喝得可真尽兴。”
“果然,少爷?”
“嗯,可不是。大家都高兴着呢。果丝还向你问好。”
“多谢粉克-诺透先生惦记着。相信他兴致很高?”
“高得不得了。要说他可是大限将至,马上要改口管沃特金·巴塞特爵士叫岳父啦。不过他叫总好过我叫,吉夫斯,他叫总好过我叫呀。”
这话是有感而发。至于原因呢,容我解释一下。几个月前,庆祝牛剑赛艇那天晚上[3],我想给警察和其头上警盔分家,结果不幸栽在了法律手里。在拘留所的木板床上睡睡醒醒地过了一夜,第二天就被带到勃舍街法庭,重罚了五镑银子。那位裁判官给我判了这么个惨无人道的刑罚不说,还在法官席上加了不少侮辱人格的按语。要说这位裁判官不是别人,正是巴塞特老爹,果丝那位未婚妻的父亲。
事后我了解到,我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批客户了。没过几个星期,他就从某个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款子,然后就退休搬到了乡下。这个嘛,至少是官方说法。我私下以为,他有今天全是仗着贴膏药似的贴着罚款不放。这儿五镑那儿五镑的,可想而知这么些年来攒了多少。
“那位暴脾气你总不会忘了吧,吉夫斯?不好对付啊,嗯?”
“或许沃特金爵士在生活中并非如此令人生畏,少爷。”
“不见得。不管搁在哪儿,地狱之犬永远是地狱之犬。咱们别说这巴塞特了。今天有信没有?”
“没有,少爷。”
“电话通信呢?”
“有一通,少爷。是特拉弗斯夫人打来的。”
“达丽姑妈?这么说她上城里来了?”
“是,少爷。夫人表示希望少爷尽早回话。”
“我有个更妙的主意,”我热情地说,“我亲自去见她。”
半小时后,我就信步踏上了她府宅的台阶。管家赛平思给我开了门。此时此刻,我怎会想到,跨过这道门槛后,再不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工夫,我就要卷入一场纠葛,伍斯特的神魂将要经历前所罕有的考验。我所指的这场险恶风波涉及果丝·粉克诺透、玛德琳·巴塞特、巴塞特老爹、史呆·宾、哈·“没品哥”·品克牧师、一只十八世纪的奶牛盅以及一本棕色的皮面小本子。
不过,进门的这会儿,我对这场临头的大难还全然不觉,平静的心湖上也不曾笼罩上一丝乌云。此时,我正憧憬着和达丽姑妈小聚。以前大概也提过,达丽姑妈是我所尊敬的好姑妈,万万不可混同于我那位阿加莎姑妈——她可是吃碎玻璃瓶子、浑身罩着带刺铁丝的人。和达丽姑妈东拉西扯,不仅是智力上的享受,此外还有一个叫人翘首以盼的前景,那就是八成能哄她留我用午饭。达丽姑妈家的法国厨子阿纳托手艺精湛超群,因此能扑进她府上的食槽一向是对美食家的诱惑。
我穿过厅堂,看到晨室的房门敞开着,只见汤姆叔叔正在倒腾他那些银器收藏品。有那么一小会儿,我琢磨着要不要过去打声招呼,问候一下他的消化近况——这个毛病叫他深受其害。不过理智很快占了上风。我这位叔叔一见到侄子就要拉着不放,滔滔不绝地谈论什么壁饰烛台啦、叶形装饰啦,不用说还有涡卷雕饰、环饰圆形深浮雕、串珠缘饰什么的。因此我认为,还是缄口为妙,于是便一语不发地过门不入,直奔书房而去——刚才听下人说达丽姑妈正窝在那儿。
只见我这位老亲戚正埋首校样,只露出一头波浪卷儿。众所周知,我这个和蔼可亲、人见人爱的姑妈操持着一份周刊,也就是有教养、高品位的女性阅读品《香闺》。我还曾撰文一篇,题为《有品位的男士怎么穿》。
她闻声抬起头来,见猎心喜般地发出一声“哟嗬”。想当年在狩猎场上,就是这一嗓子,让她扬名于阔恩、派齐利和跟英国狐狸过不去的诸大猎场。
“嘿,丑八怪,”她开口,“什么风把你吹来了?”
“老姑妈,听说你有话要吩咐。”
“我可没叫你突然闯进来打扰我的正经事。打个电话不就得了?估计你有预感,知道我今天忙不开。”
“你是想问我能不能来吃午饭的吧?不用担心,我很乐意,一向如此。阿纳托给咱们准备了什么呀?”
“反正不是给你准备的,你个小馋虫。今天中午我约了小说家波摩娜·格林德尔来用饭。”
“我很乐意见见她。”
“哼,你见不到。今天这事儿只有我和她两个人面谈。我想请她给《香闺》写个连载。至于我找你呢,是叫你去布朗普顿路的一家古董店——过了小礼拜堂就是,很好找。我要你去古董店鄙视一只奶牛盅。”
我没听懂,心里只觉着面前这位姑妈正在胡言乱语。
“去什么做什么?”
“店里有一只十八世纪的奶牛形的奶盅,汤姆今天下午要去买。”
我顿时眼前一亮。
“啊,是件银器是吧?”
“对,奶油壶一类的玩意儿。你去店里叫他们拿出来给你瞧,然后对着那东西表示轻蔑。”
“目的何在?”
“当然是弄得他们心里没底啦,笨蛋。好让他们疑惑、心虚,然后才好砍下一点价钱。买得便宜,汤姆心里就高兴。我要他保持好心情,因为要是能签下这位格林德尔写连载,那我可得叫汤姆出一小笔血本。这些畅销女作家漫天要价,真是罪过。好了,马上给我赶过去,对那玩意儿摇头吧。”
我对好姑妈们一向言听计从,但是此刻我不得不表示吉夫斯所说的nolle prosequi[4]。虽然吉夫斯的醒神饮品如施了魔法般见效,但即便是服用之后,也没法叫人大摇其头呀。
“摇不得,今天不行。”
她盯着我,右边眉毛充满谴责地上下挑动。
“哟,怎么回事儿?哼,要是你昨天灌多了黄汤,脑袋不胜摇晃,撇撇嘴总可以吧?”
“啊,那成。”
“那快去吧。还要倒抽一口冷气,再‘啧啧’两声。啊,对了,还要说它看着像是现代荷兰玩意儿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我怎么知道?据说这种奶牛盅最要不得。”
她住了口,若有所思地打量我可能略似行尸的面孔。
“这么说,你昨晚又花天酒地去了,是不是,我的小山雀?真不可思议,每次见你,你都像是刚从堕落场回来。你有没有离了酒盅的时候?睡觉的时候也喝着?”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