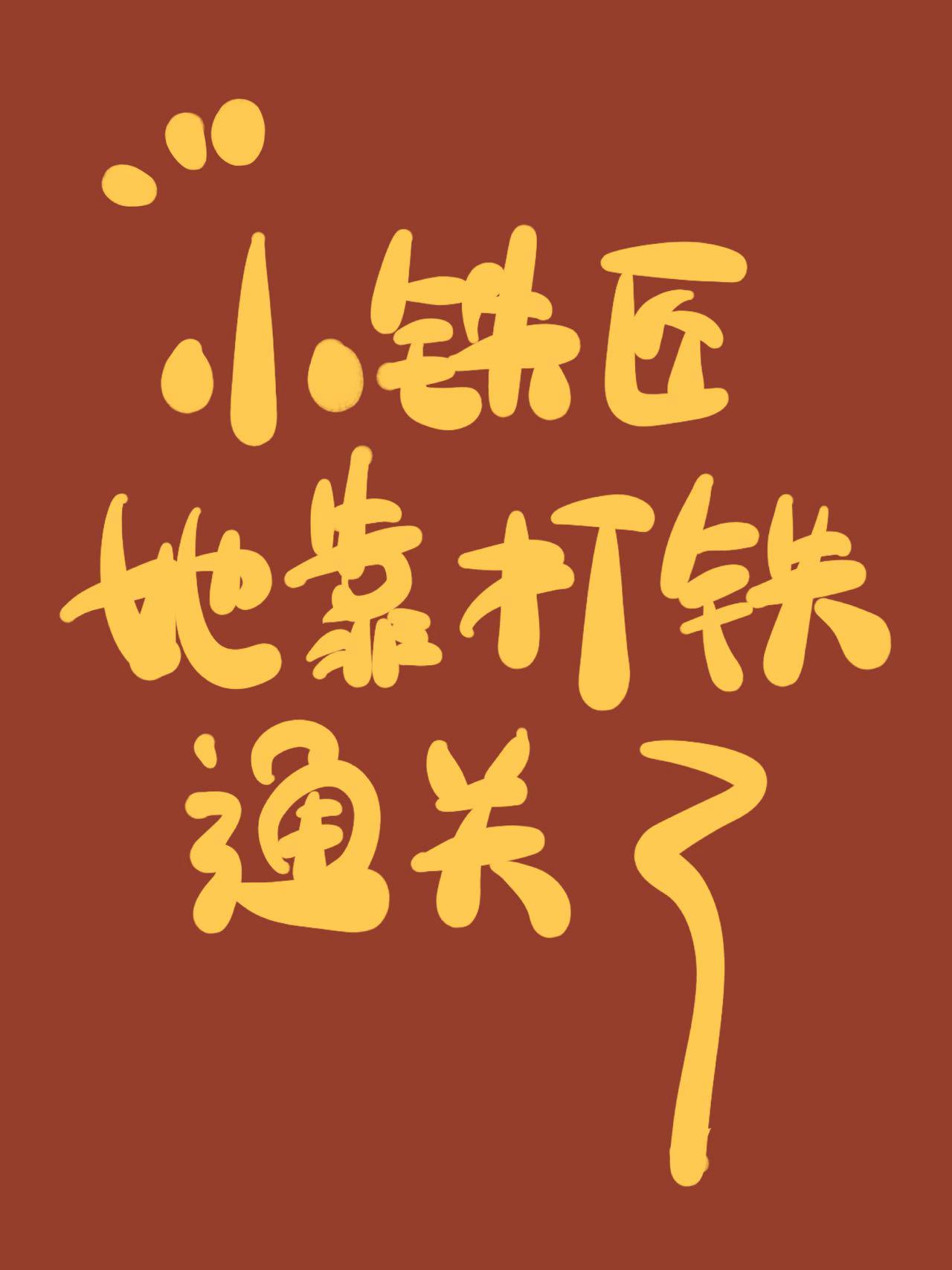阜朝,永纪七年,钟州城上沅县,卯时三刻。
于鸢又被前院叮呤咣啷声吵醒,作坊里的锻锤的声仍是络绎不绝,铁蛾随声溅落,如流星璀璨易逝,她凭铁跕上被敲打的声响,便知现下已是几时、那器物已锻打到何阶段了。
于鸢翻身坐起,定了定神,她已到这个世界两月有余,瞧着眼前的陈设,仍觉不真实,是的,她穿越了,穿到了个从未听闻的朝代。
她所处之地即边疆,此地战乱,危机四伏一触即发,人人心悬在嗓子眼儿,百姓日夜提防惴惴不安,唯恐有外患打入。
于鸢身处兵荒马乱,常常自觉如履薄冰,好在原主为铁匠户之女,虽非富贵人家,但家中亦有个打铁作坊维持生计,也不至她无处安度。
于鸢本生在非遗打铁花世家,打铁花技艺代代相传,偏偏她又是个女孩儿,打铁花所需铁水必是1600度高温,若因操作不当,不免被烫伤烧伤,这对学徒而言却是家常便饭,而她自小不畏烧伤与否,仍凭着经年毅力和精湛技艺,以实力说话,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束缚。
打铁花到她这代已是第十九代,她虽才二十有余,却为打铁花的传承发展操碎了心。为打铁花能被世人记住,也防其消失大众视野,毕业后于鸢谢绝高薪工作,选择回老家打铁花。只要公园、景区一有节目预设单,她就踊跃报名,博得一彩。
听闻京市月底有一为期三天的大型非遗会展,分为室内与室外,各类非遗传人现场展示制作环节,于鸢自是不愿错过此机会,多次往返会展提交申请,却每每被主办方以铁水高温危险为原由,将其拒之门外,终未能拿到一名额。
但若就此放弃她便不叫于鸢了,她回家不出三日,便又去到了会展现场极力争取,展厅现下还十分空旷,各类活技将整个大厅分开来,于鸢穿梭在工作人员中,觅着主办人李先生。
“请问李彭先生今天来了吗?”于鸢随机询问一工作人员。
“李先生在室外场地,出门往东二百米。”
“谢谢。”于鸢火速向外小跑,不远处便见得李彭与一西装革履的人在交谈,她笃定二人为生意伙伴,念着若能与其搭上话,那打铁花入场几率也会由此升高。
随着距离逼近,于鸢瞥着李彭身旁之人,身量高挑、打扮清爽,漆黑西装内的衬衫在日光下变得有些亮白晃眼,待看清那人模样时,于鸢脚下一顿。
此人名叫傅少青,现是上市地产公司的金牌销售,业内人士无人不知哪人不晓。于傅两家几代世交,但到了他们俩这儿,却交得如仇人一般,兵戎相向。
他大于鸢两岁,却不曾听得这小女唤上自己一声哥哥,他也的确德不配位,自小便爱逗弄于鸢,时常把她说得梨花带雨,长大后二人亦是不见则已,见则免不了一场唇枪舌战,而论此专业,于鸢自然每落下风。
于鸢自觉当真是冤家路窄,为避不必要的麻烦,她选择自动过滤傅少青的存在,径直对着李彭,“李先生,我是……”还未等她全然道出,便被李彭揽下。
“小姑娘我记得你,也已多次说明了打铁花不能入场。”李彭说着,一边瞥着腕表。“不必再说了,回去吧。”
一旁的傅少青已然心神领会,“李哥,这里我来说明,你先去忙吧。”
于鸢见着李彭离去的背影,欲追上前,“李先生!……”却当即被傅少青拦下,“你还是那么执拗。”
她被迫驻足,也觉不好过于纠缠,此遭也便如此了。于鸢转头斜睨着傅少青,“你怎么在这?”晦气。
傅少青闻声双手插兜儿,一副拿捏之态,“这室内外场地便是李彭通过我才包下场的,你说我怎么在这儿。”
于鸢得知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广交人脉,如此,倒也说得过去。“那、你能不能帮我争取到打铁花的位子?!”她脱口而出。
“我帮你?”
于鸢心里一咯噔,顿觉有些跌面儿,又不得不如此尽力一试。
“主办方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?”
她有些泄气,咬牙道,“说我铁水温度过高,怕、怕伤了游客。”
“不仅如此。”傅少青双手抱胸,一副傲人精英之姿展现无遗,他喝声道,“室外场有织布、染布、弹棉花、竹编等,哪个能经得住你的火星飞溅?”
“我会将铁花控制在指定区域内的!绝对不会飞溅火星影响秩序的!”于鸢据理力争。
“即便你技艺纯熟,但你怎么百分百保证一点儿闪失都没有?且打铁花所需占地面积、勾得上室内四五个项目了!打铁花,又占地、又有患,你说你该不该有?”
“这是京市首次非遗会展,为确保万无一失,只得如此,我是不会替你说情的,真出了事儿,还不够我给你善后的,当然,我也不会为你的愚蠢买单。”傅少青说罢便转身离开,“没商量。”
于鸢像个霜打的茄子般杵在原地,傅少青虽姿态清高,但逻辑缜密句句在理,她被怼得哑口无声,只得在心中暗自腹诽。
此番于鸢悻悻而返,心中对傅少青的厌恶又翻一翻,简直巧言令色,毫无人性!
·
几日后,于鸢接到了个未知来电。
“请问是于小姐吗?我是京市非遗会展的主办人李彭,我们几日前见过的。”
于鸢猛然提起了精神,“是我!你好李先生。”
“于小姐,您此前提过的打铁花,之前考虑到铁花白日不好尽兴观赏,现已开设非遗夜场游园会,想邀请您到场参演,请问意下如何?”
于鸢有些受宠若惊,对此事已不抱有希望的她,竟不想还有柳暗花明之时,“好!我去,谢谢您。”
“于小姐,真是不显山不露水,此前是李某人失礼了。”电话那头言辞恳切,“那,不日还请于小姐前来商量相关事宜。”
于鸢听得前半句一头雾水,但也未过多纠结,沉浸在喜悦中。“好。”
非遗夜场游园会则是为白日会展所产出的成品,例如糕点、手工艺品等的售出,开设的游园会,游客可吃着逛着,还有打铁花节目助兴。于鸢感叹不愧是生意人,如此有经商头脑,此番下来,游客可在此逛上一整天。
待一切相关事情已尘埃落定,很快来到游园会当天。
于鸢到时入场,望着已由工匠搭好的花棚、心中跃跃欲试。虽她经年未间断精进技艺,但从未像她父亲一般“中彩”。当铁水一棒击中花棚顶部的老杆,烟花长鞭于空中炸开鸣响,对打花者而言至高荣耀,亦标志着其技艺纯熟,可独当一面。
于鸢认为每次打铁花,都是中彩对她发起的挑战。
围观群众皆是翘首以盼,届时四下漆黑,唯有记录设备泛起夜中星点,于鸢将预备的生铁搁进身旁的熔炉,反复融搅着,随着工匠卖力拉风箱鼓风,生铁逐渐化为铁水。
她双手各拿一花棒,一手上棒盛上铁水,便火速跑到花棚下,一手拿下棒用力向上猛击,只见木棒中的铁水瞬间隔空绽开,现出绚丽夺目的花火,在火花即将殆尽之时,于鸢身后的十几个打花者一棒接着一棒,来往熔炉花棚之间。
铁水接踵而至冲天空而起,簇簇铁花连连不绝,叫人一睹为快。围观游客纷纷叫好,将转瞬即逝的惊艳珍藏在匣子相机中。
于鸢望着花棚,又至挑战——“中彩”,她舀起一花棒铁水,碎步至跟前,眼神坚定,瞄准中央的老杆,下棒向上狠敲。
她视线紧跟铁水,直冲而上,在遇到棚顶的柳枝后迅速崩散炸开,流星如爆。
“中彩了!中彩了!”
“小于!你中彩了 !”
随着铁花飞溅、炮声齐鸣,于鸢才反应过来,自己击中了老杆。
她僵直杵在原地,仰头观着火花与烟花,耳边一片哗然,多年的执着终在这刻得到释然。
于鸢有些恍惚,仅着眼于的火花灿烂。
此时打花者的技艺仍在不停上演,随着铁水的不断递进,火光也愈发愈演愈烈,直至幻为一片白光,茫茫散开。
白炽的火光刺得于鸢睁不开眼,她侧头以掌心相抵,白光更甚,撒在其全身。
片刻,待白光如烟殆尽,于鸢周遭却已是翻天覆地,以至于今日回想,她亦觉惋惜、荒唐。
惋惜于自己终于“中彩”,却无以延续那荣光;荒唐于她真的穿越了,且迷途不知如何返。
·
于鸢每每庆幸,这原主与自己不仅同名同姓,相貌也完全相同,方便行事,但两女之性情相差甚远,让她倍感困扰。
于鸢自小被散养着,性情从不拘着,遇事处变不惊总有自己的法子,说的少,做的多,促使她至长成后有些不善言辞,随性中带着些固执己见。
而原主父亲于常杉人到中年方得一女,妻子不幸难产而亡,父女俩相依为命,于常杉常觉亏欠,对原主宠爱有加,任性些也是有的,以至原主嘴上从不饶人,时常冲上欺下而不自知。
虽原主任性而为,但面对老父亲时仍是爱之敬之,且在打铁活技上却不曾懈怠,家中无子,她也愿自担接管,亲力亲为。
原主的性情形同于鸢的精神外放,而于鸢的纯良亦是原主之内核,二人相辅相成,骨子里有着相同的坚韧。
于鸢继承原主意志,接手打铁作坊,亦是对于常杉敬爱有佳,近来,于常杉因着作坊之事过度操劳、又加之人将至古稀,一时熬不住,现已病倒在床,于鸢每日于塌前照看,毫不轻怠。
·
阜朝现已入秋,于鸢晨起下榻,她今日倒能落得两耳清闲,不必围在铁跕前听那打铁声,而是去衙门,取知县拨款分发给匠户的银两。
因着边疆战乱,朝廷兵器吃紧,铸造局产出的兵器已供不应求,便令各地私有作坊的工匠们予以支援。
于鸢所在的上沅县,唯有于家一户打铁作坊,于常杉历代打铁为生,虽规模不大,但国难当头自当砥砺尽一份力。
待她梳洗完毕,望着镜中已被时代熏陶得古色古香模样,不禁有些哀凉。现下于鸢身无长物,为不至彻底同化沦陷,即便秋日里,她亦身着不算保暖的布衣,以微微凉意时刻提醒自身处境。
于鸢请安过于父,途径院前作坊时,碰上从中守株待兔窜出来的李逸,“我同你一起去!”
“眼下边疆动荡,衙门乱得紧,你一女子独行,多有不便!”李逸拍着胸脯,一副“这个家没我就得散”的气势。
“走吧。”于鸢应着,李逸加快向前递了两步,与其并排而行。
李逸年十九,与原主一同在院中长大,亦是于常杉的得力干将,造诣更是胜过于鸢。多日来,他因着性格开朗活分,综合掉了于鸢的不善言辞,很是讨于鸢欢喜。
半个时辰后,俩人徒步至衙门口,正要踏足,便被身后马蹄声引去。
二人回过身去,只见一人驰骋着黑马,丝毫没有避忌之意,冲着俩人直奔而来。...